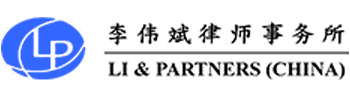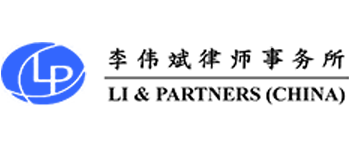研究出版

一、 概述
我国目前只有企业破产制度,尚未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现行的《企业破产法》于2006年8月27日颁布,在起草的过程中,有关个人破产的条款曾经被纳入立法考虑,但最终还是被排除在外,因为立法机关认为,实施个人破产制度需要具备相对完善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以及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而当时我国尚未在这些方面做好准备。[1]多年来,除了法律学者不断强调个人破产制度的优点,提倡在我国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外,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也积极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以解决法院判决执行难的问题。最近有消息称,全国人大财经委表示,将于2019年6月成立立法起草小组,以修订《企业破产法》,有关议题可能包括在我国建立个人破产制度。[2]
在现代破产法理论中,个人破产制度总是包含破产免责制度。破产免责制度也被称为“重新开始 (fresh start)”政策,其显著特征是:债务人无法偿还的剩余债务将在破产程序结束时被免除,债务人能够从这些债务中被解放出来,并在财务意义上“重新开始”他的生活。 许多司法管辖区规定了在最终解除破产之前有一段期间(“破产期”),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的破产期通常为破产开始后4年;[3]一些司法管辖区则规定了更短的破产期,例如在美国的清算案件中,债务的免除通常发生在提交申请日之后约4个月。[4]上述特征使得我国民众担心,如果将免责制度纳入个人破产制度,将会引起公众对于债务人滥用个人破产制度逃废债务的顾虑。在当初起草2006年《企业破产法》时,立法机关没有同时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就反映了整个社会的这种担忧。
一般认为,我国民众对破产免责制度的担忧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强调“欠债必还”或“父债子还”。[5]偿还债务不仅是法律义务,也是道德义务。[6]因此,债务免除的概念与中国传统的偿债文化相矛盾。其次,社会诚信环境状况不佳,使人们不免担心破产免责制度会被债务人滥用来逃避还款义务。[7]
既然有上述担忧,那么我国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时是否应当将破产免责制度纳入其中呢?为回答这个问题,笔者参考其它相关司法管辖区有关个人破产和免责制度的做法,并在本文中逐一讨论了以下内容:(1)过去三十年国际上关于破产免责制度的立法趋势,(2)具有与我国相同或相似传统文化的其它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实践,以及(3)其它国家或地区为防止破产免责制度被滥用所采用的法律机制。在此基础上,笔者得出的结论是:传统文化观念并不会是我国民众接受破产免责制度的真正障碍,运作良好的个人破产制度也很难被欺诈性债务人所滥用,真正影响我国民众接受破产免责制度的另有其它因素;在个人破产制度中纳入破产免责制度是国际立法趋势,也与我国国家发展政策相一致,政府与社会应当继续努力排除真正影响我国民众接受破产免责制度的不利因素,使得个人破产和免责制度得以良好运作并造福社会。
二、 过去三十年国际上关于破产免责制度的立法趋势
1. 英国
破产免责制度首先由英国于1705年在其个人破产制度中创立,但当时的目的只是为了促使债务人愿意配合破产受托人的工作,特别是要债务人向受托人全面披露自身财务状况并交出所有财产以偿还债权人。[8]虽然此后,破产免责制度亦逐渐发展出基于人道主义和正义原则的保护“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的功能,[9]但英国破产法传统上仍然是对债务人怀有敌意的。[10]
然而如今,英国已经改变了他们对债务人的传统敌意态度。[11]《2002年企业法》(Enterprise Act 2002)将破产期从3年减少到1年,[12]而且取消了许多传统上加诸于债务人的权利限制。[13]根据《2002年企业法》的白皮书《生产力与企业:破产——第二次机会》所述,英国对其个人破产法的改革旨在鼓励创业精神和负责任的风险承担,以期进一步促进社会中财富的增长和就业的增加。[14]英国政府认识到,在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中,经商需承担风险并且难免会失败,因此他们减轻了个人破产的法律后果,以鼓励想要创业的人士不要害怕失败,并鼓励那些受市场或经济因素影响而失败了的创业者再次尝试。[15]
2. 其它欧洲国家
在有关制度改革方面,德国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德国曾经一直施行不包含破产免责的个人破产制度,但该立法态度到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改变,1994年制订的破产法中首次引入了破产免责制度。[16]该1994年破产法于1999年1月1日生效,破产期设定为7年。但仅在短短2年后的2001年,德国又修改了该1994年破产法,将破产期减至6年。[17]有实证研究报告指出,这种立法实践的改变与德国社会自营业务比率提高的现象相一致。[18]
除英国和德国外,许多其它欧洲国家的立法实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表现出类似的变化趋势。例如,芬兰、奥地利、比利时和荷兰分别于1993年、1995年、1998年和1999年将破产免责制度纳入其个人破产制度中;[19]爱尔兰以前规定的破产期长达12年,[20]在2012年的改革中将该期限大幅缩短至3年。[21]
解释上述立法变革趋势的理由可以在欧盟于2003年发出的题为《绿皮书:欧洲的创业精神》的倡议中找到。该倡议指出创业精神对促进欧盟繁荣具有重要作用,包括能够促进增加就业、 提升竞争力、释放个人潜能、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等,并且强调欧盟非常需要发展创业型社会。[22]作为欧盟创业政策的一部分,个人破产制度与社会保障和税收制度一同被作为用于平衡创业风险和奖励的机制。[23]欧盟认为:“失败是经济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24]在债务人欺诈或不诚实的情况下,破产须面对严格的法律后果是合理的,但对于诚实的创业者来说,他们承担风险的行为应该得到奖励而不是受到惩罚。[25]基于此,欧盟建议考虑采取适当措施,例如:缩短破产期、取消对破产者的某些限制等,以减少破产的负面影响,从而鼓励创业精神。[26]
3. 新加坡
新加坡于上世纪90年代初对其当时已实施了一百多年的破产法进行了修改。新的破产法于1995年生效,随后于1999年被进一步修改。[27]《1995年破产法》对“诚实但不幸”的破产人,尤其是那些因经商失败而破产的创业者,放宽了破产免责的规定。 [28]
该破产法修改的背景是新加坡政府正在努力推动建立更有利于创业的营商环境。作为推动该国家政策的措施,《1995年破产法》在帮助新加坡政府鼓励创业者有计划地承担风险,以及促使公众对于经商失败更加宽容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9]
4. 小结
综上,将破产免责制度纳入个人破产制度,或者进一步放宽已有的破产免责制度的规定,是明显的国际立法趋势,目的是鼓励发展社会创业精神。在当代,经济日益为知识所驱动,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将鼓励创业作为重要政策。[30]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个人破产制度已不仅是无担保债权人用来收债和惩罚债务人的法律程序,而且可以是政府实施鼓励创业相关政策的有效机制。
近年来,我国也一直积极在全国推行鼓励创业的政策。《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即明确指出,今年政府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鼓励创业和创新”。[31]根据上述破产免责制度在鼓励创业方面的积极作用,建立一个包含破产免责制度的个人破产制度,符合并且有助于实现我国政府的发展目标。
三、 具有与我国相同或相似传统文化的其它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实践
在东亚,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家或地区,日本和韩国则是传统文化深受源自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对于亚洲社会而言,破产法基本上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外来法律文化,而上述所有国家或地区都已建立了自己的个人破产制度,并且所有的个人破产制度均已包含破产免责制度。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相关实践经验对我国考虑是否采纳破产免责制度应具有参考价值。
1. 个人破产制度和破产免责制度的建立及影响
通过回顾这些国家或地区分别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过程,可以发现就制度建立本身而言,很少涉及传统文化因素。这些国家或地区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更多是出于历史原因。
具体而言:香港的个人破产制度是英国殖民者在19世纪末根据英国破产法建立的;[32]新加坡的个人破产制度也是在19世纪英国殖民时期根据英国破产法建立的,并且部分受到澳大利亚破产法的影响;[33]日本于1920至1930年间通过向德国、奥地利和英国学习而建立了个人破产法律体系,并于1952年受美国占领当局的影响纳入了破产免责制度;[34]韩国的个人破产制度建立于20世纪初的日本殖民时期,[35]其《1962年破产法》以日本破产法为蓝本制定;[36]中国台湾地区则与韩国相似,其个人破产制度最初也是在日本殖民时期根据日本破产法建立的。[37]
根据有关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表的研究报告,[38]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被宣告破产是一件没面子的事,并且对于商人来说,这还是一件有损商誉的事。因此人们对个人破产感到耻辱,通常不愿意被宣告破产。此外,儒家传统思想倾向于避免发生法律诉讼,因此破产案件在过去相对较少。但是,学者们也指出,随着时代变迁,个人破产所带来的耻辱感一直在减少。以香港为例,耻辱感的消退主要可归因于其国际化的环境、人口流动性大等因素,[39]并且人们也越来越将破产视为“经济周期的内在部分”[40]等等。
对于个人破产法与中国传统的债务偿还观念之间的冲突,在上述学者研究报告中有受访者指出,中国传统观念在相关问题上与个人破产法并行存在,即使个人破产法规定了破产免责,偿还债务仍然是道德义务。[41]但是受访者也指出,传统文化的影响正在减弱。
2. 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1997年底至1998年初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极大地改变了上述亚洲国家或地区对个人破产法的制度设置以及民众对于个人破产的态度。举例如下:
(1) 香港
统计数据显示,亚洲金融危机后,个人破产申请数量显著增加。1989年至1996年间提交申请的案件总数仅为3,958件,但2002年该数字已升至26,922。[42]而债务人主动申请个人破产的案件数量更是从1994年的仅仅3件急剧增加到2002年的25,138件。 [43]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巨大的变化不仅是金融危机导致的市场经济状况不佳所致,而且也受到1998年7月1日生效的《1996年破产(修订)条例》的影响。[44]
旧的香港个人破产法遵循英国破产法的传统,对债务人采取敌意态度,严厉的破产制度使破产人很难获得解除破产。[45]而且,立法对债务人的怀有敌意的态度难免会增加个人破产所带来的耻辱感。在过去,除了传统文化因素,严厉的破产法也可能是破产申请案件很少的原因。
相比之下,新的破产条例改变了对债务人的态度,放宽了传统上严厉的个人破产规则,使破产人获得解除破产的难度降低。[46]此外,新的破产条例将提交破产申请的理由从债务人的“不法行为”更改为“有问题的财务状况”,这反映出立法对于个人破产的态度取向已变得中立。[47]在这种情况下,破产程序的性质实际上已从对债务人的惩罚机制转变为债务人的复原(rehabilitation)机制,[48]这有助于减少个人破产所带来的耻辱感,从而鼓励无力偿还债务的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
(2) 新加坡
新加坡的有关统计数据可以进一步表明立法取向和政府政策对个人破产案件数量的影响。如上所述,新加坡于1995年颁布了新的《破产法》,其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鼓励创业的政策。在这个背景下,新加坡法院从1988年至1997年间,每年平均颁发的个人破产令数量为1,500个,但此后的1998年、1999年和2002年颁发的个人破产令的数量分别为2,841、3,094和3,588个,呈持续上升趋势。[49]
(3) 日本
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在2001年和2002年个人破产案件申请数量从160,741件增加到214,996件,增幅约为35%。[50]
对于该时期日本的社会现象,有评论指出:在经济高增长期间,个人破产是带有社会耻辱的概念,[51]但在经济长期衰退期间,日本社会开始将破产视为仅是经济周期的另一面。[52] 这个评论似乎也适用于上述其它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情形。
3. 小结
通过参考上述东亚有关国家或地区的立法实践,笔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债务偿还观念应不会成为人们接受破产免责制度的真正障碍。原因总结如下:
首先,人们对个人破产和免责制度的传统观念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并且可以通过立法、政府政策、及社会宣传等方式来影响及改变。
其次,人性是务实的。如果个人破产和免责制度能够有效地鼓励社会创业、促进经济繁荣,进而改善人民生活,那么人们不太可能会拒绝接受它们。
第三,坚持传统观点,例如“欠债必还”,可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特别是当债务人确已无力偿还债务时。此外,在父子依靠同一块农地生活的古代农业社会中,“父债子还”这句话可能还有其合理性,但在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这样的观念早已经失去了经济和法律基础。
第四,没有证据表明与中国有相同或相似传统文化的东亚国家或地区有关偿还债务的传统观念对个人破产和免责制度在当地社会的运作和发展形成实质性的阻碍。
注释
[1] 贾志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草案)>的说明——2004年6月21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6年第7期,第577页。
[2]《修订破产法应重在地方政府归位》<https://mp.weixin.qq.com/s/r_6TjyHxfwx6CloYr3WMXg>(2019年4月24日浏览)。
[3] 香港《破产条例》(香港法例第6章),第30A(2)条。
[4] Margaret C. Jasper, Individual Bankruptcy and Restructuring (2nd edn, Oceana Publications 2006), 33.
[5] 许德风,《破产法论——解释与功能比较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14页。
[6] 齐明,《中国破产法原理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 38页。
[7] 参见注5,第519页。
[8] Ian F. Fletcher, The Law of Insolvency (5th edn, Sweet & Maxwell 2017), para 1-020.
[9] Douglas G. Baird and Thomas H. Jackson, Cases, Problems and Materials on Bankruptcy (2nd ed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0), 29.
[10] 参见注8,第1-040段。
[11] 参见上引注, 第1-040及1-041段。
[12] 参见英国《1986年破产法》(Insolvency Act 1986)第279条及英国《2002年企业法》(Enterprise Act 2002)第256条;另参见:John Armour and Douglas Cumming, ‘Bankruptcy Law and Entrepreneurship’ [2008] American Law and Economics Review, 310.
[13] 参见注8,第1-043段。
[14]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of the UK, ‘Productivity and Enterprise: Insolvency – A Second Chance’ (July 2001), < https://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http:/www.insolvency.gov.uk/cwp/cm5234.pdf> accessed 4 May 2019, para 1.1.
[15] 参见上引注。
[16] 参见注12,Armour and Cumming 文, 第304至305页。
[17] 参见上引注,第305及342页。
[18] 参见上引注,第330页。
[19] 参见上引注,第312页。
[20] 参见上引注。
[21] Müge Adalet McGowan and Dan Andrews,‘Insolvency Regimes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OECD Working Paper, 1 July 2016),<https://www.oecd.org/eco/insolvency-regimes-and-productivity-growth-a-framework-for-analysis.pdf> accessed 4 May 2019, Page 31.
[22]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Green Paper: Entrepreneurship in Europe’ (21 January 2003), <http://ec.europa.eu/invest-in-research/pdf/download_en/entrepreneurship_europe.pdf> accessed 4 May 2019.
[23] 参见上引注,第24页。
[24] 参见上引注,第12页。
[25] 参见上引注,第12及24页。
[26] 参见上引注,第24页。
[27] Victor Yeo and Pauline Gan, ‘Insolvency Law in Singapore’, in Roman Tomasic (eds), Insolvency Law in East Asia (Ashgate 2006), 376.
[28] Roman Tomasic, ‘Singapore’, in Roman Tomasic and Peter Little (eds), Insolvency Law & Practice in Asia (FT Law & Tax Asia Pacific 1997), 143.
[29] 参见注27,第376页。
[30] 参见注16,第304页。
[31]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March 2019), <http://english.gov.cn/premier/speeches/2019/03/16/content_281476565265580.htm> accessed 4 May 2019.
[32] E.L.G. TYLER, ‘Insolvency Law in Hong Kong’, in Roman Tomasic (eds), Insolvency Law in East Asia (Ashgate 2006), 218.
[33] 参见注27,第375及376页。
[34] Stacey Steele, ‘Insolvency Law in Japan’, in Roman Tomasic (eds), Insolvency Law in East Asia (Ashgate 2006), 16 and 20.
[35] Soogeun Oh, ‘Insolvency Law in Korea’, in Roman Tomasic (eds), Insolvency Law in East Asia (Ashgate 2006), 66.
[36] Soogeun Oh, ‘Comparative Overview of Asian Insolvency Reforms In the Last Decade’ (April 2006),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GILD/Resources/Oh5.pdf> accessed 5 May 2019, 8.
[37] Angus Francis and Neil Andrews, ‘Insolvency Law in Taiwan: The Interplay between Official and Unofficial Law’, in Roman Tomasic (eds), Insolvency Law in East Asia (Ashgate 2006), 131.
[38] Roman Tomasic, ‘Hong Kong’, in Roman Tomasic and Peter Little (eds), Insolvency Law & Practice in Asia (FT Law & Tax Asia Pacific 1997); 参见注28; 亦参见:Roman Tomasic and Angus Francis, ‘Taiwan’, in Roman Tomasic and Peter Little (eds), Insolvency Law & Practice in Asia (FT Law & Tax Asia Pacific 1997).
[39] 参见上引注,Tomasic, ‘Hong Kong’,第126页。
[40] 参见上引注,第127页。
[41] 参见上引注,第128页。
[42] Charles D Booth, ‘Current Trends in Consumer Insolvency in Hong Kong’, in Johanna Niemi-Kiesilainen, Iain Ramsay and William Whitford (eds), Consumer Bankruptcy in Global Perspective (Oxford and Portland, Oregon 2003), 187.
[43] 参见上引注。
[44] 参见上引注,第188页。
[45] 参见上引注,第189页。
[46] 参见上引注,第191页。
[47] 参见上引注,第193页。
[48] 参见上引注。
[49] 参见注27,第378页。
[50] 参见注34,Stacey Sttele文,第15页。
[51] 参见上引注,第14页。
[52] 参见上引注,第15页。
免责及版权申明
本文章仅为交流之目的,不构成李伟斌律师事务所任何形式的法律意见。欢迎转发本文章。如需转载或引用本文章的内容,请注明文章来源。